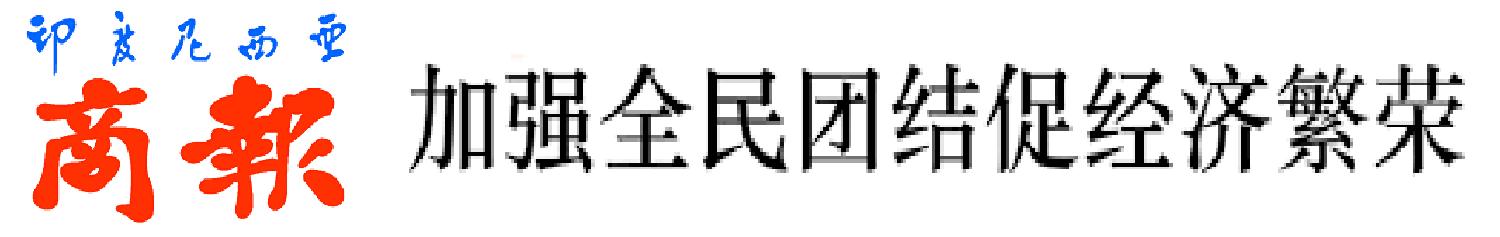社论:信贷扩张乏力且风险大 银行靠国债票息稳收入
-

成为国家财政融资顶梁柱的国家银行业,似乎必须继续“加班加点”。其作用不再仅仅是信贷中介,更是国家债务工具的主要吸纳者。
截至2025年6月底,银行持有的国家有价证券(SBN)总额飙升至1199.96兆盾,占流通总量的19.02%,较2024年底的17.41%有显着上升。
仅2025年上半年就额外购买了148.56兆盾,这表明银行流动性管理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。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这一转变恰恰发生在信贷发放增长放缓之时。截至2025年5月,信贷发放同比仅增长8.43%,低于2024年底的10.39%。
另一方面,第三方资金(DPK)的吸收也未见明显复苏,停滞在4.29%的水平,略低于去年底的4.48%。
这意味着,银行业可能正面临资金开始受限的现实,但仍然选择了安全稳妥的道路,即购买政府债券,而非冒险向生产性部门发放信贷。
这种选择当然事出有因。家庭消费放缓、贷款利率上升以及制造业尚未复苏,是导致信贷扩张意愿低迷的主要因素。
资产质量风险也笼罩着每一项贷款决策。在净息差(NIM)收紧的压力下,许多银行选择通过国债票息来确保收入。
这一举措得到了银行减少持有印尼央行短期工具(如SRBI)的支撑,2025年前五个月该工具持有量减少了22.65兆盾。显然,银行正将其偏好从短期货币工具转向期限更长的国家债券。
然而,这种保守策略留下了一个重大问题:如果银行不愿承担风险,谁来为实体经济融资?如果这一趋势在2025年下半年持续,那么称印尼经济在生产性领域面临隐性流动性危机,并不过分。
仍在承受高成本负担和国内需求压力的商界需要更大的融资支持。然而,银行非但没有提供信贷,反而在强化其作为国家“债主”的地位。
从财政角度看,政府显然获得了短期利益。当沉重的税收目标和难以压缩的支出导致赤字空间日益扩大时,银行对国家有价证券(SBN)的认购意愿就成了救星。
然而,本报认为,依赖金融部门的国内资金来填补赤字并非没有风险。当国家预算融资中由银行业承担的比例过大时,国家将面临“挤出效应”(crowding out)的风险,即私营部门在争夺融资来源时处于竞争劣势。
这种情况可能形成悖论。一方面,政府需要实体经济作为新税基和经济增长的支撑。但另一方面,财政策略却在吸走本应注入实体经济的流动性。
与此同时,银行正处于漩涡之中,面临着是维持资产质量还是刺激高风险信贷增长的选择。那么,我们的金融体系还能容忍这种“求稳”的策略多久呢?
印度尼西亚银行(央行)和金融监管机构(OJK)理应更严格地监控这一动态。资金在SBN的配置与信贷扩张之间的失衡,可能给未来经济增长造成潜在压力。
更何况,如果将此与部分领域不良贷款率(NPL)上升联系起来看,银行发放贷款无疑会更加审慎。因此,政策方向不应被动,需要提供特殊的激励措施,以确保农业、中小微企业(UMKM)、制造业和医疗保健等优先部门仍能获得应有的融资渠道。